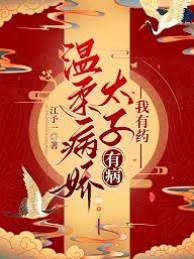《榮婚(重生)》 第70章 第 70 章 于高朋滿座訴說愛意
第70章 第 70 章 于高朋滿座訴說意
西江月.....
夏芙低垂的羽微, 素來平靜的眼眸一度緒暗湧。
那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臘月中旬的一日大雪紛飛。
弘農程家堡的宅子外,種了一片枯竹,竹竿被大雪彎, 伏在地上有如山丘。
的琴案正對著窗口, 已經是練第七遍了, 快亥時, 實在舍不得撒手。
他就坐在側,一茶白的厚袍子, 緄邊繡著銀竹紋,襯得那張冷白的面孔極其矜貴俊。
其實不大敢看他, 那雙漆黑的眸眼極穿力, 好似被他看一眼, 便無所遁形。
腳邊的炭盆火勢漸衰,程明昱無奈,從一旁鐵桶裏鉗出幾塊炭火又擱進去, 炭盆登時發出呲呲聲響,火苗竄起來。
“還要彈?”
夏芙明知他已不耐, 卻是輕輕抿著在他看不見的地方笑了笑, 然後點頭,
“是,總覺我彈得不大對味,了些什麽..”
“家主, ”忽然偏轉過眸,一雙秋水般的眸眼盈盈注視著他,
“您能彈一段給我聽聽麽?”
方才他只是信手撥了幾個音調,就格外好聽,有一種渾然天的瀟灑, 明明是同樣一把琴弦,為何區別這般大,想聽一整段,當然更想聽一整曲,可不敢說。
大著膽子起,讓開位置,亭亭立在那兒,算是在“”他了。
程明昱看了一眼那把琴,暗暗嫌棄了一番,
“這般喜歡《西江月》,下回我捎來琴弦,彈與你聽便是。”
夏芙聞言心裏滋生一綿綿的熱浪。
聽人說過,家主極擅音律,也收藏了一把舉世無二的焦尾琴,這樣的人,用最好的琴弦,再彈一首最的《西江月》,想一想,夏芙子都要飄起來。
Advertisement
立在窗下,低垂著眉眼,按捺住喜悅朝他輕輕點頭,“嗯,我知道了。”
餘卻見他立著一不,夏芙視線往上移,忽然與他目對了個正著。
他明明白白看著,好似
在問還踟躕什麽。
夏芙眼珠子轉溜一圈,才想起二人之間的“正事”,慌忙拍了下腦袋,提著擺面頰發燙往床榻去。
害一時沉迷于彈琴,忘了時辰吧。
這麽晚了,他還要回去呢。
夏芙暗暗掐了自己一把,走到拔步床,瞥見裏頭被燈火照得通明,臉上登時一熱,立即折回去吹燈。
跟在後往這邊行來的程明昱,差點被折返的撞個正著。
他連忙偏過,就看著匆忙吹了燈,那笨手笨腳的樣子,整得好似在。
他無奈搖搖頭。
熄了燈,屋子裏陷黑暗,各自自在多了,他們習慣了黑暗,均輕車路上了塌。
這一回他比往日都要久,那泉眼好似怎麽都掘不盡,一泓又一泓溪流漫蓋裳床褥,害臊地捂住臉。
他總是輕而易舉便能探到底,很想控制住,嗓子卻怎麽都不聽使喚,後來回想起簡直無地自容,等他走了許久,蜷在被褥裏想,下回,下回一定要矜持些。
次日醒來人就不大有神。
心想定是昨夜鬧得晚了些。
練琴練得晚,他又要得久,便弄到子時往後了。
嬤嬤來催了,夏芙方起塌,心裏還想著後日的約定,早膳沒用多也沒覺出異常。
天冷路,老太太沒讓去請安。
在院子裏歇了一日。
第二日還在下雪,窩在被褥裏更不想起來。
眼盼著第三日的到來。
這一日天可憐見放了晴。
嬤嬤過來照顧起居時,多了一句,
“今日家主出了門,說是莊田那邊出了事,要去看一看。”
Advertisement
心裏就有些失落,不會爽約吧。
這種緒一直持續到午後,忽然吐得昏天暗地,只當自己著了涼,喝了幾口熱水溫在被褥裏,到底是驚婆母,婆母是穩妥人,帶著府上的大夫來了。
看著大夫,忽然一愣。
再然後,大夫給搭脈,只聽見喜脈二字,腦子裏一片漿糊。
老太太喜極而泣,抱著哭天搶地,
“好孩子,咱們總算是懷上了,總算是懷上了,你不必再罪了...”
不必再罪了....
夏芙怔愣當場。
直到今日都無法形容那一刻的心。
被老太太摟在懷裏,磕在消瘦的肩骨,遲遲笑了笑,“是喜事。”
一夜北風吹。
坐在琴案著月門口,被雪彎的竹條堵死了他來時的路,從約定好的戌時一直坐到亥時,膝蓋都麻了,一貫伺候的那位老嬤嬤心疼地抱著毯子裹在上,將擁在懷裏,
“不必等了,家主不會來了。”
滾燙的淚珠砸在琴案,碎水花。
“只待你懷孕,我們不再相見。”
“好,有了子,我一定不再叨擾家主。”
十九年過去了。
悉又陌生的旋律,跟蠶一樣一點點往四肢五骸鑽,往心上纏。
夏芙深深閉上了眼。
臺上的程明昱已試過音。
長公主聽聞他要彈琴,已轉過子面朝琴臺的方向。
拋開對這個男人的愫,程明昱是音律大家,他當衆琴,便是一場視聽盛宴。
這樣的盛況,豈能錯過?
將食案擡著換了個方向,程亦安只能陪著轉,轉的片刻,瞄了一眼對面的夏芙,和雲南王坐著沒。
起調是幾個音符,高手與尋常人的區別是,明明是幾個很簡單的音符,程明昱彈起來,音符之間流暢,曲調仿佛一縷煙從耳畔一而過,輕而易舉將所有人的心弦給勾住。
Advertisement
僅僅是起手,他就表現出得天獨厚的功力。
真乃天籟之音。
這是一首膾炙人口的曲子,被古往今來的音律大師封為十大名曲之一,講述的是一對兩小無猜的青梅竹馬,對彼此暗生愫,尚未來得及稟報父母,提親納采,朝廷一紙征兵的詔書發下來,男子背負行囊奔赴戰場,臨行前二人在竹林互訴衷腸,約定護守終,只可惜三年過去,傳來男子戰死的消息,方將孩兒嫁出去了,又是五年過去,當年莽撞青蔥的年,一躍為人上人的大將軍。
待他功名就回鄉,斯人已嫁,當年活曼妙的,包著一頭紗巾抱著一個襁褓的孩子,正在田間幹活。
兩兩相,唯有淚千行。
所有憾均訴在那綿綿的風聲與細雨中。
程明昱沒有將這種憾描繪得如何哀婉悱惻,起手過後便是一串如流水般淙淙的曲音,仿若面前翠竹掩映,幽窗下寶鼎茶閑繞指涼,有琴音穿山渡水而來,攜著一抹淡淡的清涼與憾,拂化這殿熾熱的暑氣。
長公主的目一直落在那雙手。
不聽曲,不看人,僅僅是這雙手,白皙修長,指骨分明,指尖在琴弦是那麽游刃有餘,好似游戲人間的謫仙,輕輕彈開一指,便是人間春。
目忍不住往上,移至那緋紅的襟,那裏自是一團仙鶴補子,沒有人能夠把袍穿得這樣好看,他該是天生的架子,寬肩窄腰,夏日袍用的輕薄的緞面,極是服帖,能清晰勾勒出他拔清雋的形。
隨弦而的寬袖,恍若林間的風,秋日的雨,富春江上一抹浩瀚的煙雲,閑庭信步。
回想當初為何一眼相中程明昱。
他有一種渾然天的,不似雕琢,克謹,是山巔的雪,雪上的松。
Advertisement
多年過去了,這個男人的韻味就像是深巷的酒,歷久彌新,越發引人勝。
他的琴如同他這個人,不會狂妄不羈,不會肆無忌憚,恰恰是克制延續到極限時,輕輕一撥,足夠人心魄。
一見程郎誤終。
長公主自嘲地笑了一聲。
不知是何人將珠簾給開,能讓眷們清晰看到那道清絕的影。
熾熱的夏風從開的殿外掠進來,化不開他眉間那抹霜雪,彈指間有那麽一種參世事茫茫的悲憫從容,仿佛明知這是一曲得不到回應的孤鳴,一場遲到的不曾宣之于口的意,卻還是忍不住走一遍來時路,將它全部訴在這把琴裏。
彈得太好,甚至覺察不到他任何嫻的技巧,仿佛每一個音符為他而生。
石衡之妻,素來推崇程明昱書法的石夫人,與側的秦夫人道,
“程大人這樣的男人,只適合供著,哪個人能心平氣和做他的妻子。”克妻也就不奇怪了。
“可不是?只要程公活著,‘風華絕代’這四字,只有他擔得起。”
即便是程明昱的兒,與他相最多的程亦喬,著這樣的爹爹依舊如癡如醉,
“長姐,你知道我這輩子最大的幸運是什麽嗎?那就是投胎為爹爹的兒。”
程亦歆笑道,“也是最大的驕傲。”
西江月既然是家喻戶曉的曲子,就意味著在場所有善琴者,均彈過,禮部尚書孔雲傑從始至終不曾睜眼,甚至手指輕輕在食案叩,自顧自合曲,心裏卻想,他那侄兒拿什麽跟程明昱比。
陸栩生過去最不喜文人的這些作派,但今日實打實被岳父給折服。
就如他們習武之人使刀法到登峰造極之地步,岳父這一手琴彈得是出神化。
後的程亦彥扯了扯他的袖,低聲道,
“怎麽樣慎之,有這樣的岳父,是不是倍力?”
陸栩生氣定神閑往上方程亦安一指,
“你瞧,全場都在聽琴,就一人虎頭虎腦,可見我家安安不吃這套,安安還是喜歡我這樣的,但是大舅哥你就不一樣,有這樣的父親,我看你才力如山。”
程亦彥苦笑不已,第一次在陸栩生跟前敗下陣來。
陸栩生說完看向程亦安,連他都被岳父的琴音化,怎的程亦安好似滿臉苦惱。
程亦安大概是全場唯一沒有認真聽曲的
人,這首曲子為誰而談,程亦安冥冥中已有知。
琴臺上的爹爹已是人琴合一,而娘親呢。
注意到夏芙雙手疊在一,指尖始終覆在那串珊瑚珠子,不曾往臺上瞟上一眼。
明明是朗月清風,鵲驚蟬鳴的意境,
他們一人端坐琴臺,衆人皆醉我獨醒。
一人默坐高席,置事外。
程亦安心裏沒由來湧上一陣酸楚。
雲南王聽過夏芙彈琴,如果說先前還只是猜測的話,那麽今日程明昱這首曲子一出,他忽然之間什麽都明白了。
夏芙也彈《西江月》。
人家程明昱哪是給皇帝祝壽,他這是在紛紛擾擾的人群中,訴說著對夏芙晦的意。
這樣的人,這樣的氣度,居高位,手掌權柄。
雲南王有那麽一瞬,突然想認輸,餘注意到夏芙指節發白發,他覆過手去,握住冰涼近乎抖的手,以只有二人才聽到的嗓音道,
“阿芙,大不了你收個外室,我也認了。”
夏芙一怔,面頰一紅掙開他的掌心,別過臉去不理會他。
曲子進最後一段,三段重音,從最開始的高激烈意境恢弘,慢慢過度至忍克制,到最後收音時,長指一,所有憾如脈脈月輝歸于雲海深。
一曲終了,餘響繞梁。
殿許久無人出聲。
是太子最先出一掌,除宗親外,所有人起朝程明昱行禮致意。
程明昱雙手搭在琴弦,心緒慢慢平複,收弦,朝皇帝施禮,
皇帝還沉浸在方才那段旋律中,掌一笑,
“這什麽?‘客心洗流水,餘響霜鐘’,今日之程公,風華無極,讓朕大開眼界!”
程明昱道了一聲謬贊,便抱著焦尾琴下臺,將琴弦給侍時,大約是那把焦尾琴很有年份,一弦往他手指崩了一下,珠順著手背下來,侍嚇了一跳只當自己沒收好,程明昱不聲按住傷,示意侍退下。
此舉恰被雲南王收在眼底,他癟癟,
“那弦怎麽就彈在手背,幹脆往脖子抹一抹不就得了。”
夏芙瞪了他一眼。
雲南王訕訕一笑,“說著玩的,說著玩的。”
猜你喜歡
-
連載355 章

攝政王的俏醫妃
他將她禁錮,溫熱的氣息灑落:“小東西,還逃不逃?”她被逼趴下,驚慌失措:“不逃了,九皇叔,我錯了!”第二天,不講信用的鳳家九小姐又跑了!戰王一怒為紅顏:“整個皇城掘地三尺,也要給本王將她逮回來!”……他是北慕國戰神,神秘莫測,權傾天下。她是一不小心跌入他懷中的小東西,從此,成了他又愛又恨的心肝寶貝兒……
38.8萬字8.18 147163 -
完結1684 章
神醫傻妃:鬼王的絕色狂妃
一朝穿越,成了廢材外加丑八怪!爹爹不疼后娘不愛。 她可是22世紀國際首席特工。 說我丑?說我天生死脈是廢材?非要逼我告訴你們這些全是裝的麼! 左手靈泉空間,右手上古神器。還有只無敵靈寵寶寶,誰敢欺負我! 屁股后面還有一個帶著鬼面的妖孽王爺~ 當廢材變天才,丑妃變絕色。驚掉一地下巴。 這一世,且看她如何覆手翻云,名動天下! 一朝穿越,成了廢材外加丑八怪!爹爹不疼后娘不愛。她可是22世紀國際首席特工。說我丑?說我天生死脈是廢材?非要逼我告訴你們這些全是裝的麼!左手靈泉空間,右手上古神器。還有只無敵靈寵寶寶,誰敢欺負我!屁股后面還有一個帶著鬼面的妖孽王爺~當廢材變天才,丑妃變絕色。驚掉一地下巴。這一世,且看她如何覆手翻云,名動天下!
154.5萬字8 454414 -
完結196 章

長安小飯館
細雨微風,青幟小店,胡姬如花。 新豐美酒,鮮葵嫩筍,金齏玉鱠。 京兆少尹林晏把目光放在那個雪膚杏眼的老闆娘身上。 一個高門仕女淪落到當壚賣酒的境地,實在可憐可嘆…… 沈韶光:美酒美食相伴,還能看過路的英俊小郎君,生活不要太美好^ 林晏面沉如水,這些五陵年少每日打扮得這般花哨,打馬街頭,鬥雞走狗,很該整頓整頓! 吃前提示: 美食,日常向,甜爽。 仍然大致以唐為背景,半架空,勿考據。
29.4萬字8 18498 -
完結192 章

引月入懷
太子嬴風假模假樣替三弟搜救未婚妻顧家嫡女,結果一無所獲。 遂冷冰冰蓋棺定論:顧今月“已死”。 事後,一向冷血恣睢的太子殿下破天荒地寬慰傷心的三弟:“斯人已逝,生者如斯。” * 顧今月重傷後失憶,她的夫君嬴風說會幫她想起一切。 “你從前眼裏只有我一人。” “無論我做什麼,你從不推卻。” “唯我是從。” 她紅着臉結巴道:“真、真的麼?” 嬴風握緊她的手,笑得意味深長。 當晚嬴風坐在顧今月床頭,黑瞳貪婪地描摹着毫無防備的睡顏。 驀地俯身湊到她耳邊低笑道:“假的,我也會變成真的。” 顧今月毫無所覺。 直到某夜她從夢中驚醒,記起一切。 她不是他的妻,而是他三弟曾經的未婚妻。 【小劇場】 顧今月捂住懷胎三月的小腹,一隻腳還沒來得及逃出大門。 身後傳來嬴風漫不經心的笑聲。 “嬌嬌,你方向走反了,我在這兒呢。” 忽然被人攔腰抱起送進裏屋,她聽見了刺耳的落鎖聲。
30.4萬字8.18 6901 -
完結23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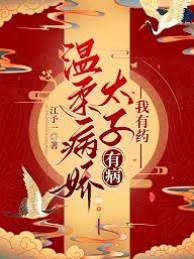
溫柔病嬌太子有病,我有藥
【古言甜寵 究極戀愛腦深情男主 雙潔初戀 歡快甜文 圓滿結局】 謝昶宸,大乾朝皇太子殿下,郎豔獨絕,十五歲在千乘戰役名揚天下,奈何他病體虛弱,動輒咳血,國師曾斷言活不過25歲。 “兒控”的帝後遍尋京中名醫,太子還是日益病重。 無人知曉,這清心寡欲的太子殿下夜夜都會夢到一名女子,直到瀕死之際,夢中倩影竟化作真實,更成了救命恩人。 帝後看著日益好起來,卻三句不離“阿寧”的兒子,無奈抹淚。 兒大不中留啊。 …… 作為大名鼎鼎的雲神醫,陸遇寧是個倒黴鬼,睡覺會塌床,走路常遇馬蜂窩砸頭。 這一切在她替師還恩救太子時有了轉機…… 她陡然發現,隻要靠近太子,她的黴運就會緩緩消弭。 “有此等好事?不信,試試看!” 這一試就栽了個大跟頭,陸遇寧掰著手指頭細數三悔。 一不該心疼男人。 二不該貪圖男色。 三不該招惹上未經情愛的病嬌戀愛腦太子。 她本來好好治著病,卻稀裏糊塗被某病嬌騙到了手。 大婚後,整天都沒能從床上爬起來的陸遇寧發現,某人表麵是個病弱的美男子,內裏卻是一頭披著羊皮的色中餓狼。 陸遇寧靠在謝昶宸的寬闊胸膛上,嘴角不禁流下了悔恨的淚水。 真是追悔莫及啊~
42.5萬字8.18 79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