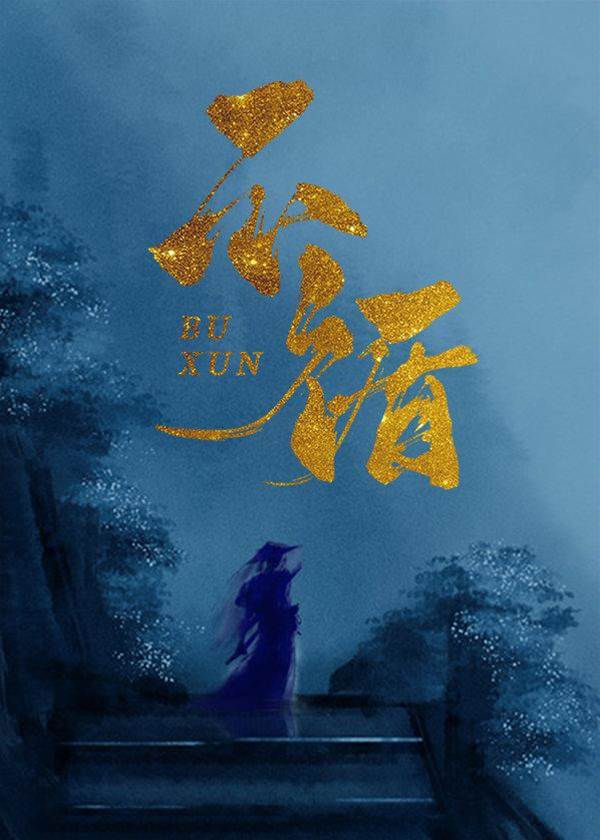《被渣后和前夫破鏡重圓了》 第 84 章
既然大的這麽快就被他找到,小的那個所在位置必然也瞞不過。
懷墟不意外他會猜到,若有如無地頷首。
“我接手脈召的時候,察覺到了奚荼子嗣的氣息。奚荼的溶族脈很強,他孩子的脈卻出乎我意料的微弱。”說到這,懷墟才將手指從杯盞邊緣放下來,隨意搭在膝頭,似笑非笑丟出一道驚人消息:“它給我的反饋,就在蘿州城。”
他看向陸嶼然:“在你邊。”
陸嶼然像是被針尖刺了下,緩緩坐直,慢慢瞇了下眼睛,問:“什麽意思?”
懷墟手指一擡,半段細長的線頭在指尖盤轉蠕,蠕的姿勢很像蟲蠱,在半空中試探時速度卻很快,幾乎能看見一點微末紅殘影,它能曲能直,穿過涼亭石桌徘徊在陸嶼然邊,繞著他轉了一圈,最終掀他的右側袖擺鑽了進去。
腕骨一側暴在空氣中。
陸嶼然皺眉垂眼,下意識抵任何,但礙于某種猜測,最終沒有拽出線條甩在桌面上。
過涼亭中的燈,男子腕骨勁瘦流暢,力量深深潛藏,著幹淨的冷白,先前有袖邊遮掩倒也看不出什麽,但此刻被線條一掀,腕周側兩三個疊淤青齒痕的印記若若現。
十分曖昧。
線條不再彈,像是嗅到了目標一樣安然趴在這圈齒痕上,懷墟指尖一勾,線條就消彌在兩人視線中。
什麽意思,已經很明顯不過。
陸嶼然眼底蓄積起翳。
懷墟和陸嶼然年齡相差無幾,也算是舊相識,彼此能說得上話,他政務纏,沒什麽看熱鬧的心思,然如今看之事實在覺得荒誕,不免提了下:“認真的?”
這一天裏幾起波折,事事有關溫禾安,陸嶼然忍不住擰了圈腕骨,又甩了下,作間難免外洩出點躁意,眼神銳利而直接。
Advertisement
不認真,他總不能是覺得好玩。
懷墟笑了下,弧度淺淡:“找到奚荼,我們就準備回程了。王族的‘相’與能力對外皆是,不能外洩,溶族脈特殊,按理說,我要將奚荼的兒帶回去。”
“但我赴萬裏而來,如今九州腹地,敵多我寡,就罷了。”
他停了下,才接著說:“我就不見了,問問要不要見見父親吧,如果我應得沒錯,兩道溶族緣,已經有許多年不曾接過了。”
“我王族的規矩,正好讓奚荼說一說。”
聰明人跟聰明人打道,好在不必拐彎抹角,壞在稍不注意就被抓住重點,一擊即中。懷墟若是說別的,陸嶼然大可直接拒絕,可他說起父之間,這是溫禾安的事,只有自己能做決定。
“這段時間不行。”陸嶼然從石凳上起,面朝垂落的紗帳,道:“奚荼是你們的人,明日你見過他之後,所有人都撤離九州,他可以留下,待事解決完再轉向巫山,經九州防線回歸異域。”
懷墟居高位,已經很與人如此明火執仗,有來有回地推拒試探,事實上,除了靈漓派系的堅定擁護者,無人敢忤逆他,他跟著站起來,思索了會,垂眸漠然:“給我個理由。”
“傳承要開了。”兩道視線皆如雷霆霜,短兵相接時各有各的考量,陸嶼然沒藏瞞什麽,道:“我不允許任何東西在這時候擾的心境。”
溫禾安面對的強敵太多,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強大的實力是保全自己的絕對倚仗。
需要心無旁騖的獲取這份力量。
年天驕初遇,滿腔炙熱,事事都在為心上人考量,耐心,細致,算無策。
然而從來真心能得幾分回報。
Advertisement
懷墟遮下眼底不以為意的荒寥,輕掃了眼他的背影:“沒想到你也有這一天。”
“我也沒想到。”
湖水流聲徐徐,陸嶼然回,因兩人立場全然不同,注定談公事比私事多得多,難得有語氣和緩的時候,此時撥了下簾紗,似笑非笑:“以為你和靈漓鬥生鬥死,誰知突然管起了妖骸的事。你這是在替誰耿耿于懷。”
懷墟坐回椅子上,神莫測,搭在茶盞上的三手指挲著花紋,半晌,哂笑一聲。
陸嶼然將一個白瓷瓶放在桌面上,說:“外域的傷藥在九州管不了什麽用,別帶著一腥味到招搖。先湊合用,我這裏暫時沒更頂級的傷藥。”
巫山帝嗣何曾在這方面有過短缺,懷墟看了他一眼。
陸嶼然眼皮一耷,說話時又冷又酷:“給我道了。”
他手指了指懷墟肩胛位置,也是覺得有意思:“你這又是怎麽了?誰還能傷得了你?”
懷墟真正笑了下,臉上每線條都鮮豔生起來,一雙眼卻凜然逢冬,在致明旖的五下有種格格不的沉郁之:“還能是誰。”
“陛下親自出手。”他指尖散漫地摁了下肩骨位置,好似渾然覺不到疼痛:“說起來,還是我的榮幸。”
陸嶼然聞言靜默,他從前就不懂這個人和靈漓之間的糾葛,現在和溫禾安在一起後,算是有經驗了,依舊不懂——也不想懂。
他對自己現在和溫禾安的狀態很是滿意,任何話都可以說明白,任何矛盾都可以攤開來解決。
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有多喜歡,也同樣能到的喜歡。
“後天我進境,五天後回來,回來後我找個機會見見奚荼。”陸嶼然最終說。
懷墟看看擺在面前的瓷瓶,慢條斯理道:“這麽好心,打的是這個主意?”
Advertisement
陸嶼然反問:“他以異域之,在九州蟄伏百年,我不該見?”
無可挑剔的說辭。
懷墟心知他要問的,想問的絕不是這些,卻沒有深究。他們作為九州與異域舉足輕重的人,關系一直控得各有餘地,張弛有度,有些不那麽嚴重的,雙方都會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日後真出了事,才要有商有量互通有無。
“陸嶼然。”懷墟喚了他一聲,神淡淡的:“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跟你提及,兩域在妖骸之上的研究或許可以深研究,你我皆有利。你好好考慮考慮。”
陸嶼然作一頓,開簾紗往外走,撂下一句:“走了。”
==
溫禾安先去月流的院子裏見了徐遠思。
第一次見面徐遠思狀態不好,才從王庭的控制中,休息也沒休息好,渾渾噩噩竭力清醒著將自己認為關鍵的說了,跟倒豆子似的,也分不清什麽重點不重點。
他能想到會在短時間和溫禾安見第二次,也知道會整合手裏目前有的線索問他一些更為細致的東西,但此刻在燭火下見剔的眼睛,還是有些晃不過神來,側了側頭,遲疑地問:“你說什麽?”
溫禾安坐在綠藤邊的寬椅上,示意他也坐,跟好友敘舊般,他問,便耐心地重複:“我才從珍寶閣出來,聽說你們徐家日常做買賣不,其中牽連的也不。我今日來,就是想聽聽這些事。你知道多,都說出來。”
徐遠思驚疑不定,就差舉手澄清了:“誰說的?話可不能說,我們家什麽時候牽扯了——”
他們家都快被害死了。
他邊說邊看溫禾安的臉。
“不牽扯傷天害理那一環,參與最後收尾的也算。”溫禾安彎下將一被風吹到腳邊的藤條拂開,側臉靜安然:“我是在世家長大的,世家做的什麽易我知道,這次來不是為了興師問罪。”
Advertisement
徐遠思明白這個意思了,他張了張,生怕不知道,道:“二主,溫禾安,我們家是收了別人錢的,簽了天字契,手印都摁了,不能對外說半個字。你問問林十鳶,生意場上誠信立足啊,這樣日後誰還敢……”
“你若不說,傀陣師徐家可能就于此代終結了。”在有限的時間裏,溫禾安不會任由時間在題外話上逗留太久:“徐家留下來的那些人,顯然撐不住傀陣師門戶,你們家哪還有立足之地。”
徐遠思啞然無言,半晌,狠狠一撐額頭,嚨吞咽了下:“我不知道,我接手族中之事也沒幾年,這個你知道。”
溫禾安看了恨不得指天發誓的徐遠思一會,半晌,彎彎,脊背松懈下來靠著椅子,輕聲說:“是,這個我知道。所以我只想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徐遠思,別的事我都不必知道,我只想知道最關鍵的。”
“你沒對我說實話。”
徐遠思鎖眉。
“你先前和我說,金銀粟的陣心與傀陣師融合可為這事,是你們家的絕,這樣的絕,我卻從別的地方知道了。當時我以為,是徐家旁支勾結王庭意取而代之,可後來想想,既然是絕,旁支知道的可能也不大。”
溫禾安手指自然搭在寬椅椅邊,輕輕點著,聲音不疾不徐:“消息是你們自己出去的?你們和王庭早在這方面有接?”
的聲音很好聽,散在夜風中,卻讓徐遠思起了一後背冷汗:“不管是王庭,天都還是巫山,他們若是起了用的心思,且計劃牽扯之大能聖者都出手,要做自然就只做效果最好的那個,我若是他們幕後的決策者,你想想,我第一個會去接誰。”
徐遠思完全沉默下來。
“九州之上,誰不知道金銀粟是一大奇跡,一個陣法,世代傳承,庇護後嗣,屹立不倒。林十鳶說它是世間最為特殊的,創造它的人,在這方面,鑽研必定最深吧。”
徐遠思一直沒坐,就杵著站在燈下,面龐模糊,像只被踹了淋了雨還要強打著神撐面子的落難狗,溫禾安每說一句,他就落魄一分。
到最後,他勉強扯了下角:“你怎麽比幾年前還聰明。”
“大概是這幾年不順心,謀謀見得多了,想得也就多了。”溫禾安擡眸看了看夜空中閃爍的繁星:“半個時辰後我有別的事要做,我這次想聽毫無瞞的真話。這件事上,我繞的彎子已經足夠多了。”
“你不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的人,自己好好想一想。”
從始至終表現得隨和,語氣跟閑聊一樣,然而一琢磨,尤其是後兩句,徐遠思能嗅到危險之意。
徐家一垮,他現在也不是徐家主,溫禾安只是看起來溫和無害,但因為合作過,他有幸見過大幹戈起來是多麽鐵石心腸。
現在是說也得說,不說也得說,他本沒得選擇。
徐遠思心飛速衡量,好在兩人是友非敵,有著一樣的目的,提早的開誠布公有利于接下來的行,他本來也是打算在撇幹淨徐家的前提下慢慢給線索的,既然現在撇不開,那便說吧。
人都沒了,維持個清正不阿的正派名聲有個屁的用。
他微微一咬兩側腮幫,這下也不矯了,拽過那把寬椅拖了幾步,發出令人牙酸的嘎吱聲,他恍若未聞,一屁坐下去,還沒開口說話,先深深吸了口氣:“我們家可能確實跟有一些牽扯,但那絕不是本意。”
“我們家雖然從不自詡清正名門,但培養教育起家中子弟,向來是規規矩矩,什麽能做,什麽不能做,講得明明白白。你說得沒錯,因為能力特殊,有不人惹出了事會我們收尾,涉及些戰爭,還有許多勢力重金邀約,但不是所有找上門來的錢我們都能收。幾百年前,我們家就定下了規矩,凡有勢力傀陣師出手相助,戰後不得屠城,不得大規模斬殺驅趕流民,這都是寫在天字契上的。”
“九州戰不休,難民越來越多,每年秋季,稻谷,我們家也會拿出一大筆靈石來換食救助疾苦。我不是邀功,只是想提前說,徐家不說純白無瑕,但還有良知,禍害衆生,我們沒有能耐阻止,但絕不會助紂為。”
猜你喜歡
-
連載1320 章

重生後休夫改嫁,顛覆你江山
前世,謝南梔傾盡所有助夫君上位,庶妹卻和夫君聯手斷送了將軍府上百口人命。 一朝重生,她手握絕世醫術,背靠神秘組織,發誓要讓背叛她的人付出代價。 渣男上門?她直接甩休書退婚!姨娘下毒?她直接讓她自食其果!庶妹蛇蠍心腸?她直接撕下她的臉皮踩在腳下。 她一心複仇,無意間發現七皇子慕傾寒一直在背後幫自己? 謝南梔:又幫我打臉,又給我權勢,還多次救我出險境,你是不是想接近我,是不是想利用我,是不是想陷害我? 慕傾寒:不是,你媽吩咐的。 謝南梔:…… 沒想到她還有一個身份成謎的大佬親媽!
125.2萬字8 11953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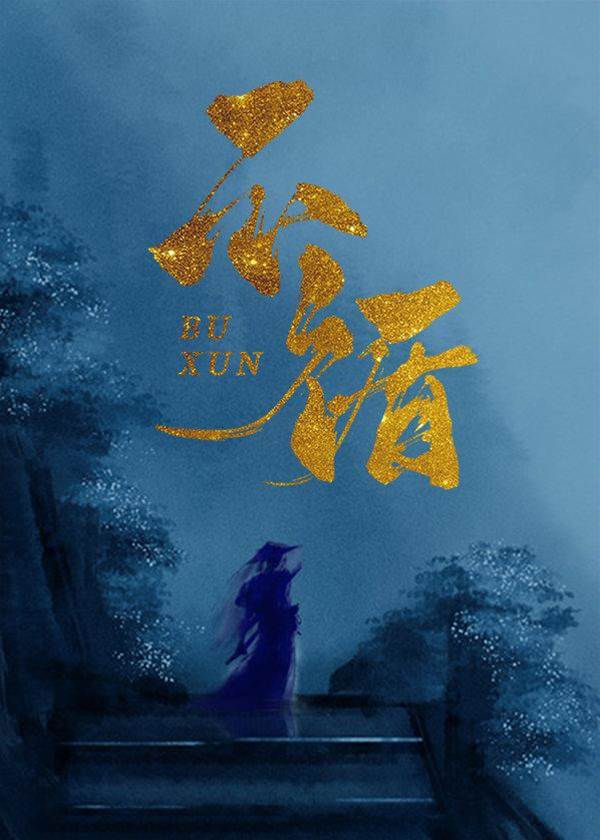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50004 -
完結228 章

囧妃馴夫:美男太兇猛
穿越古墓,她蘇醒在萬年尸尊的墓穴之中。 財富相貌權力地位他樣樣皆有,無數女子前仆后繼為他殉葬。 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個個貌美如花,打破腦袋只為能陪他一夜。 可這逆天的家伙卻唯獨喜歡她,將她當成寵物般養著,還哄著誘著讓她喊主人。 她問我憑什麼。他答憑我喜歡。 她斥你太霸道。他笑但你喜歡。 他的溫柔,她全部收下。 他的寵溺,她全部收下。 他的霸道,她勉強收下。 可她只是在他棺材里躺了幾夜,什麼也沒做,腹中怎地就珠胎暗結了?! 陌縛眼光凌厲“這是誰的孩子!” 古慈汗如雨下“可能大概也許是……你的?”
59.2萬字8 8929 -
完結216 章

不夜墜玉
師蘿衣與錦鯉小師妹爭斗。 不甘心比了一輩子,敗了一輩子。青梅終究比不過天降,最后連她的竹馬未婚夫也不可救藥地愛上了小師妹。 破廟瀕死,無人殮骨。 就很氣啊! 她驟然想起,很久之前,自己也曾贏過一次:她不可描述了小師妹看得和眼珠子一樣的凡人兄長
33.5萬字8.46 1008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