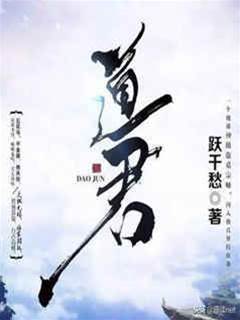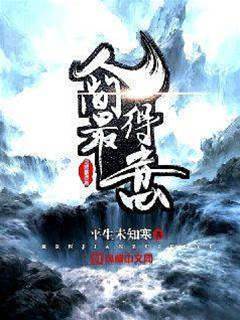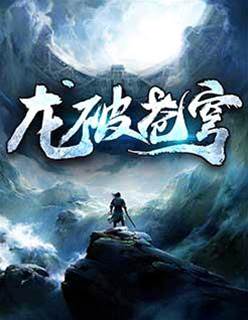《劍來》 第一千一百零九章 此山從此便姓陳
丁道士便了靴子,坐在廊道,淹頭搭腦,有點無打采,無奈道:“小道現在已經分不清玉璞和仙人兩個詞匯了。”
他是在乘坐薛天君符舟途中,與諸位道士一起復盤,丁道士才猛然驚醒,自己是仙人境啊!哪是什麼小心被日月煎人壽的玉璞?
謝狗恍然道:“想來是咱們山主對你比較刮目相看,愿意多打磨打磨你這小牛鼻子道士,見你不識趣,自己不開竅,只好找個由頭,讓你返回山中,是好事,別苦著一張臉了。”
謝狗的言外之意,很淳樸的,你可別不識抬舉,不分好賴,小心被砍啊。
屋陳山主,前天煉劍,是第二次被了。
上次是脖頸被勒出一條目驚心的槽。說是驚人,不是這點傷勢如何夸張,而是那個躲在重重影中的幕后十四境,能夠無視落魄山護山陣法和扶搖麓此地的重重制,在半點不出蛛馬跡的前提下,就讓一位止境歸真一層的武夫,到這種程度的傷勢。第二次下狠手,更是直接將心神沉浸于煉劍途中的陳平安背脊拉開一道可見白骨的傷口。這讓負責護關的謝狗氣得咬牙切齒,所幸陳平安再次放棄煉劍,還是老神在在,沒有半點頹廢,打開屋門,坐在廊道,跟謝狗閑聊了一會兒。
虧得陳平安有一把籠中雀。
不然閉關一事的半途散功,后果不小。輕則天地靈氣往外泄,重則清減一道氣或是折損數十載道行。
只說靈氣流散一事,自古就是放出容易收回難。每一記法神通的施展,確實都是從儲蓄罐往外砸錢。
將天地間渾濁與清靈二氣分開,需要煉氣士一點一點剝繭,境界高者,自然相對輕松,可是下五境煉氣士,是這一件事,就要耗費無數,若無家學或是明師指點,沒有師門傳下法寶靈,既無仙府道場的地利,又無人和,當然會壁,修行不順,一境有一境的關隘,更怕走上岔路,只說修煉一件本命,譜牒修士,都有現的修行次第,山澤野修上哪兒“聞道”去?有師承相授的,那真傳一句話,沒有領路人,就是迷障千萬丈,消磨的鬼打墻,還不是最可怕的,就怕修行誤歧途,走到一條不歸路,斷頭路。煉廢一件候補本命,興許譜牒修士可以承,猶有代替之,對于“野狗刨食”的山澤野修而言,可能就是大道就此斷絕的慘痛下場。
Advertisement
所以宗字頭道場,都會最設置一座護山大陣,不同法統道脈,各峰也有各峰的陣法,層層加持,為的就是藏風聚水,歸攏靈氣,無形間清除天地間的污濁煞氣。要知道所有大陣的運轉,都是要吃神仙錢的。這筆支出,只要乘以年數,數額就會很大。這就又衍生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關于護山大陣是否能夠汲取周邊的天地靈氣,如果答案是汲取,那麼“周邊”到底是多大,歷史上幾乎所有宗門,就都有不同的選擇,都注定繞不開這個不宜對外公開的問題。
一般來說,兩座宗門之間,何止是相隔萬里之遙?就是怕“犯沖”,宛如江河互爭水道。
落魄山的選擇,極為保守,是僅僅封存天地靈氣不外泄就行,并不以大陣行“氣吞山河”之法。
當年同在州地界的龍泉劍宗,也是如此作為,可即便如此,由于兩宗地理位置過于毗鄰,如俗語所謂的一山容不得二虎,龍泉劍宗還是“被迫”搬遷出去,在外界看來,就是大驪皇室首席供奉的阮邛,必須主給劍氣長城的年輕“讓道”,不得不避其鋒芒。
山君魏檗親自幫忙遷徙山頭,居中調節的大驪宋氏,同時給了阮邛一份補償,在大驪舊北岳地界劃撥出一大塊地盤給龍泉劍宗。
在寶瓶洲其他修士看來,這一切都是合合理的。
甚至還有很多傳得有鼻子有眼睛的小道消息,說那位機緣巧合之下、一遇風云變化龍的陳山主,年時其實曾經試圖去鐵匠鋪子求個落腳地,結果被那眼高于頂的阮邛百般看不起,覺得那貧寒年沒有修行資質,死活不愿意收陳平安為室弟子,后者心灰意冷,當了沒幾天的雜役短工,阮邛就干脆將他趕走了。
Advertisement
不知何時,寶瓶洲就開始暗流傳開來幾個說法,“收徒不能太阮邛”,“看人奇準阮首席”,“放出大阮劍仙”。
這些諧趣說法,都是劉羨親口告訴陳平安的。
當時陳平安憋了半天,詢問阮師傅聽見了這些說法作何想。
劉羨認真思量一番,說阮鐵匠面無表,心無波瀾……吧。
解釋?這種事,讓陳平安怎麼解釋?跟阮師傅解釋,還是跟寶瓶洲那些傳消息的王八蛋解釋?
別讓老子當面見你們這些嚼舌頭的,小心狗頭不保!
丁道士小心問道:“前輩道齡很長?”
謝狗扯了扯角,“睡了很長很長很長一覺,錯過很多很多很多事。算不得真正的道齡。怎麼,如果是年紀大的,境界比你高,心里就痛快幾分了?”
丁道士搖頭道:“小道不會做此想,修行是自家活計。”
謝狗便順著這位小道士的說法延出去,“一個道士,眼中所見,太過盯著眼前事和手邊事,心中所見,至多是自己的將來如何如何,不太著想人之外的天地大道,至在我看來,難稱道士。”
“不是說一定要當個什麼良善好人,非要在萬丈紅塵里爬滾打,走了一遭又一遭。只是如今你們道教道家道法道士,至道祖起,再到各家各門戶的祖師爺,再加上那些個隨手可翻的道書典籍,都要求徒子徒孫們積攢外功,更有道士提出什麼八百三千功德之類的,道統法脈分出千百條,各有各的此消彼長,榮辱興衰,可既然大家都如此看待一件事,持有同一個看法,自然是因為這件事,有利可圖。我想說的真正意思,你聽不聽得懂?”
丁道士點頭道:“前輩意思,晚輩理解。”
Advertisement
謝狗嗤笑道:“可別是不懂裝懂,跟我裝蒜啊。”
丁道士說道:“豈敢。”
謝狗隨口說道:“之所以愿意與你多扯幾句閑天,是覺得你跟以前人間的那些道士,比較像,也只是相對而言了。”
“當年他們看待修道一事,真是比命更重,忍辱負重,不辭辛苦,此間滋味,你們是無法想象的了。若能在某位修道前輩那邊,聽聞道法真傳一兩句,有人便要伏地不起,痛哭流涕,毫不掩飾,既拜高人傳道之恩,也叩拜天地養育之德,更拜自己的一顆道心,不曾愧疚后一條來時道路。”
“你們就不行,不夠純粹,哭不真哭,笑不真笑,百般顧慮,千種算計,做什麼都像是跟誰做買賣似的,而不自知。”
丁道士聽聞此說,神采奕奕,心神搖曳,向往之。
謝狗瞥了眼小道士,確是可造之材。
丁道士認真思量片刻,似有所悟,抬起胳膊,向前遞出一只手掌,豎起,再輕輕搖晃一下,“如有前路先賢可稱道德者,將天地撥分出,暫以“善”“惡”強行名之,大道崎嶇難證不易得,行其善道者有早夭者,亦有行其惡道者可登高,此事最是障眼法,蒙蔽后輩學道人。但是有心計數者,便會知曉,前者事者眾,后者敗亡者多,初學道者,羽翼未,誰敢言說自己一定是登頂者,故而小心起見,需要行前者道路,久而久之,道上率先聞道者,無形中就了后學人的護道人。道上再有法統別立,路旁又有門戶另起,道就更大,路就更寬,同道行路者眾,大可以聯袂去往山巔,浩浩登天,道人以純粹道心,大煉某舊址,百人不行,千人如何?千人不夠,萬人同心!我輩道士真能如此,眾志城,萬年之后,人數,氣勢,道脈,猶勝萬年之前的登天一役,或破而煉之,以城化城,或將那天庭址大而覆之,豈是奢?三教祖師何必憂心萬年,何必散道?!”
Advertisement
謝狗板起臉嗯了一聲,輕輕點頭。
小道士可以啊,我自己都沒想著這麼多,這麼遠。
腦筋比那袁巨材好許多啊。
難怪山主會對他青眼相加,該不會是想要挖墻腳吧?
可以啊,小牛鼻子當個落魄山一般供奉,綽綽有余。
一尊無垢無暇的青衫法相,劍仙化作一道虹,掠出屋子,大袖飄搖,氣象浩渺,琉璃彩。
轉瞬間就已經遠遁百余里山水路程,丁道士耳邊余音裊裊,陳先生笑言一句,“稍等片刻,速去速回。”
丁道士問道:“這是?”
陳先生是在演練某種?
謝狗撇撇,“既然沒了神出竅的道路可走,就找個相似的法子唄,活人總不能被尿憋死。”
丁道士由衷贊嘆道:“任你萬山圍攔,自辟一條道路,說的就是陳先生這種人了。”
謝狗點點頭,“小道士,你比老聾兒更適合落魄山。”
丁道士震驚道:“可是劍氣長城十劍仙之一的那位老聾兒前輩?”
謝狗了臉頰,老聾兒名氣這麼大?在自己這邊偏要裝出謙卑、禮敬前輩的鬊鳥模樣,莫非是這位一般供奉,心不誠?
謝狗想起一事,“我們山主為何揪著你‘不求于玄’一事不放?是你有什麼難言之,切之痛,不好去求于玄指點?”
丁道士猶豫了一下,還是選擇誠懇言說此事,“我喜歡萬事不求人,當然很難做到,就退而求其次,修道之初,就給自己訂立了一個框架,比如以后登高阻,可以與羽化山只求一次,這次就用在了結丹之前,向箓城借調了二十余萬張符箓到太羹福地的道場。也允許自己這輩子與于祖師求一次,打破元嬰境瓶頸,既然可以繞過心魔,就想著以后閉關證道飛升之前,再用掉這次機會。”
謝狗說道:“這很好啊,不是死要面子,不求任何事,只是謹慎相求,如此說來,是咱們山主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了啊。”
丁道士搖頭道:“是前輩誤會陳先生了,實則陳先生用意更深。關于我的兩百載修道云水生涯,他極為肯定,給予贊賞頗多,但是陳先生也有過一句評語,可謂一針見,讓我當場汗流浹背,足可益終。”
謝狗可不會跟他客氣,“將那句評語,說來聽聽。”
丁道士深呼吸一口氣,緩緩道:“陳先生說我還不曾真正絕過,不曾真正走到過求天求地求人求己都無用的死角。所以他讓我好好思量,有朝一日臨其境,該怎麼辦,會怎麼想,轉頭回顧此生來時道路又是如何。”
謝狗了貂帽,“你也不算笨,當下有答案了嗎?”
丁道士說道:“暫無答案。但是如今有了幾個新鮮想法,通過多個正反論據去驗證最終的某個論點。”
謝狗笑道:“比如?”
丁道士微笑道:“比如長河可以倒流,于祖師在桃符山填金峰的時候,我別說求一次,都要卷好鋪蓋住在于祖師門外,每天至有一問。又例如于祖師在天外星河,我返回羽化山,肯定會隨攜帶一摞護符箓,去往天外,既能跟祖師爺求教一些問題,也能在璀璨星河間俯瞰人間,一舉兩得。”
謝狗點頭道:“你算是想明白了,原來咱們山主所謂的‘求’,與你心中的‘求’,本就不是一個概念嘛。”
丁道士使勁點頭,沉聲道:“確實如此,當丁道士拘泥于‘求人’,陳先生卻是在教我‘求道’。陳先生傳我‘問心’二字,便是教我‘問道’一事。我心目中的山中傳道,高真度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不過如此,不過如此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6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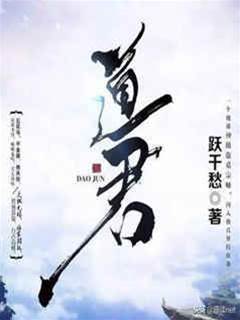
道君
一個地球神級盜墓宗師,闖入修真界的故事…… 桃花源里,有歌聲。 山外青山,白骨山。 五花馬,千金裘,倚天劍,應我多情,啾啾鬼鳴,美人薄嗔。 天地無垠,誰家旗鼓,碧落黃泉,萬古高樓。 為義氣爭雄! 為亂世爭霸! 你好,仙俠!
439.8萬字8.18 152235 -
完結9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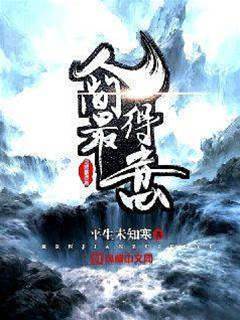
人間最得意
山河破碎六千年。攜筆帶墨,作一篇錦繡文章的讀書人意氣風發。手持破碗的道教聖人鎮壓惡妖無數,世間傳頌千百年。 遠在西邊,萬佛之地,有一盞燈籠,照亮世人前世今生。可世上怎可無一劍氣長九萬裡的劍仙?
278.4萬字6.5 16332 -
完結48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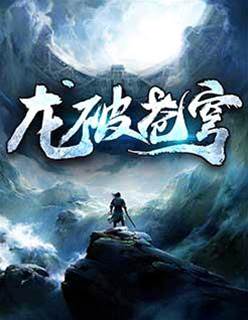
龍破蒼穹
醫毒雙絕:醫者,慈悲天下,救死扶傷,懸壺濟世!
492萬字9.41 868284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